关于旅行的家信
你看诗吗?你写诗吗?万物互联,高科技更新迭代,我们加快了生活节奏。在追求物质生活时,精神生活有时滞后。我们忙碌紧张,做到沉心静气似乎不再简单。校园中,看诗的人少了,写诗的人更

你看诗吗?你写诗吗?
万物互联,高科技更新迭代,我们加快了生活节奏。在追求物质生活时,精神生活有时滞后。我们忙碌紧张,做到沉心静气似乎不再简单。
校园中,看诗的人少了,写诗的人更少,但是诗的魅力从不褪色。
今天,让我们跟随著名诗人雪松的提问,走进江汉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柳宗宣的诗歌世界,领略诗人的风华与诗歌精神。
受访者:柳宗宣
访问:雪松
时间:2017.9
雪松(以下X):中国当代诗坛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变化发展,许多诗人借助各种各样新颖的写作观念、新鲜的写作方式高调地得到确认,这期间,有许多富有创作实力但低调的写作者沉潜下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宣称或追随什么,而是默默地探索着自己的写作道路,他们的诗名似乎没有那么响亮,但写作的成果却不容小觑,在我看来,你就是其中一员。请问,你的定力从何而来?

▲本文提问者,著名诗人雪松
柳宗宣(以下L):我和你差不多都在一个场域里写作。新诗写作进入九十年代发生了某种逆转,恰好在这个年头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写作。那年二十七岁,在一个中等职业学校执教,有了讲师职称,三室两厅的房子老婆和女儿,在这个阶段进入写作,当然不是趁热闹赶风头出于某种功利目的,它有着对人生某种规划和设计,在写作里面有所寄托,最重要的是出于对语言的热爱,当年是把写作当真正的志业去做的。在我的生活里没有什么其他吸引注意力的东西(你还有对书法的爱好除了写诗),写作成了我唯一的爱好,那可是把整个身心都用到这个爱好上。
随着与写作相伴的阅读也在不断的变迁,自己对写作的理解和态度在不断进程中得以提升,人在不停地确立否定着自己对写作的理解,内心的爱越来越明确,自己认可的方向感也在增强。渐渐地,写作出现的定力当然也越来越稳固;写作它就是一个自我建设的工程,随着对写作的理解提升,这样对外部现实就会有分野似的的态度,什么旗帜就看不见了或者视而不见,也不愿跟风头寻求什么外在确认,人会越来越相信某种进入你判断的事理,他的作品本身也在自我确认着,你会更看淡浮表的诗名,会反省早期对虚名的在意,如你所说,人好象更有定力和判断力,只对自己提要求,要完成重要的有价值的作品,作品就是地平线在勾引你去完成。说白了,可能的作品就一个写作者的新生命,它就是一个写作者的在世的盼望。
有朋友议论我的写作,说我不是跟屁虫似的先锋而是个人的先锋。这是比较客观的观察。是的,自从开始写作,找到并培养着一个爱好做下去,对外在世事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潜下心来从事写作是当成一生大事来经营的,写作和个人的生命在相互促进,写诗引寻着自己的人生的选择,在语言道路上,细想起来,它作用了我的人生,生命变成这个样子,写作整个把自己的生活或生命塑造成这个样子。
哧哧,我属牛,牛这个笨重的哺乳类是上天赋予的,你之前所说的定力是否来自我们听从或获得了上天的力量,哦,一头笨重的牛,就是不大会转弯变迁或离开,一生就田野里,缓慢笨拙的草食动物。本雅明说它是一颗土星,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桑塔格用“土星气质”来形象本雅明这类人的精神风貌,这种土星气质的人漠然犹豫、迟钝,这样气质的人与自我的关系总是处在建设中,他有着某种殉道者的执著,追求某种“失败的纯洁和美丽”。

▲本文受访者柳宗宣在武汉地铁公共空间朗诵会现场
X:你刚才谈到阅读的变迁,我感觉阅读对于一个诗写者个人写作的矫正力量很大,有时阅读像一盏灯能打开你写作的新道路,请你谈谈你阅读的变迁,以及它和你写作之间的关系。
L:和阅读的关系如同与个人生命的展开一样,它们几乎是同步的。阅读作用了我对写作的态度和视界,或者说它参与了我的生命体验和作品的生成。阅读在我的理解中是一种自我发现、词语的被看见或照亮,是对生命的某种改造和助进,它是创作的另一种方式。
从某阶段的作品你可以反观到阅读的暗中支持,阅读与写作,如同找寻生命的道途一样,它们是一个路径,只是阅读这条路径更隐蔽,因为它作用了你的精神肉身后内化成你的无意识,最后自然作用你的词语,那里有一种血肉模糊无法分析分离。
有时候我想我们家族世代农民,到了我这一辈何以要爱上了写作--可能和阅读与关,十来岁,就用一个纸箱收集在小镇上买到的连环画册。
弗洛斯特说他有些书不在手边,他就没法生活;我的旅笔袋和车上都必须带着自己的近期正在读的书,这成了一个习惯。
前些天我写了一则随笔《一生最大的愿望建设自己的书房》,是这样的,我的书房在不断地加入新的图书,同时,一些过去的藏书显露出来成为床头书。阅读或写作,它是伴随个人一生的事。
二十七岁开始写诗,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选择,写作和阅读交织在一起,自已模索拓展向前,一切皆有书的指引。有时,阅读如同一种教诲和训诫,至今我都爱读教诲录那类书,早年读《傅雷家书》,现在常读《沉思录》,《工作与时日-神谱》、前些日子读到马洛伊-山多尔的《野草集》,甚至佛教类的经书也是每日读物,它们会给你的生命以某种提醒,而且你渴望这种提醒。
X:你诗歌的节奏乃至修辞氛围都比较缓慢,有些钝,不灵巧,好像缺乏某种锐气,是个人气质造成的?还是一种风格化追求?
L:在北京工作时的一个同事在看了我的散文集后,她说,你的文章和你的性格反差很大:词句平缓语调安静,而生活中的我则急躁行动快捷。她指出的是事实,我的写作方式和我的天生的气质似乎是反着的,这可能是阅读审美带来的结果,也可能如你所说的,是某种写作风格化的愿景。
有时候重温张曙光为我的诗集写的序,他对我的写作做了细微的分析,从对日常性的观照到词语的运用,我以为他说到点子去了。
这些年的写作过程中,我总是在受之于阅读审美带来的喜好和规范,或一种内在自我要求,渴望着某种运用语言的方式,而这种对语言的态度和观点在不断地丰富生成与拓展之中。
X: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朦胧诗之后当代汉语诗歌发展最为关键的十年,许多新的写作方式纷纷涌现,许多新的文本深刻确立,那十年对于你的诗歌创作意味着什么?在那十年中,你的生活和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十年对你后来写作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L:我对九十年代新诗现场有些了解蛮有感情,在一些评论文章里我曾专文论述过九十年代新诗的文本的迁变。在供职新诗研究所干事,不可能泛泛谈新诗,我把注意力放在对九十年代以来新诗的关注上。对八十年代的成名的诗人私下里没有多少感情。之前我说了,九十年的诗人们的写作突然发生了逆转,从外部现实到我们写作者的语言现实,完全区别开八十年诗人们的写作(在此就不做具体的分辨)。
就个人写作来说,在这十年里完成了某种转型。一九九五年,当写作完《一个摄影师的冬日漫游》这首长诗,觉得自己爬过了某个山头,进入某种敞开的视界,在对过去超越的同时确立了某个阶段的写法。那些年我在县城写作视野完全是超出了地理上的囿限,漫游这首诗是在外地长途旅行归来完成的。
现在反观何以形成那种语言的转向,来自于当时涌入写作圈的译本和同行们的写作间的呼应。国内的诗人的直接呼应那是很自然的事了,记得当时有个名叫蜀光的诗人的作品对我有某种唤醒作用,当时在《诗林》杂志读到他的作品,后来我才知道蜀光就是张曙光(他一度用这个名发表作品)。我以为程光炜编辑的那个九十年代诗新读本把张曙光的诗放在前面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是开启了新诗一些新的东西,他写诗好象在七十年代末就开始了,他一直在摸索新的写法找寻他个人的风格,所以他的作品一出来,让人觉得与八十年代的作品构成某种断裂,他觉得开启了一代诗风,和他的诗友们一起以作品本身扭转了新诗某种走向。对张曙光我一直心存感念,今年我编辑的《新诗学》,搞了他一个研究专辑。九十年代过去二十多年了,其诗学资源要清理保存。
有搞评论人将《上邮局》视为我的代表作,这首诗是在一九九九年完成的,回想起来,在那十年里,在一个围墙内的校园里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从事着诗歌阅读和创作,也留下了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现在想来,离开小城到北京寻发展,与写作存在某种隐在的关系,好象写作和生活都遇到了某种困境,确实要寻求变化,后来到了北京。如果我还停在那里写诗,可能会保持那个良好的状态,可以持续地往那个路径走下去,可能更多有深度见其特性的作品会写作出来,但也说不定,我想表述的是,我离开那里,相对安定的环境没有了,到了北京新的环境当然要经历一个动乱不定的日子;我的《上邮局》正好呈现了我生命里的某种转变,诗用词语纪录那个时刻。

▲柳宗宣个人作品集
X:你说对八十年代成名的诗人没有多少感情,这是个诗学问题,还是个历史认知问题,抑或是一个情感个案?
L:我说过了,八十年代的诗歌场域,我不在其中。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观1986-1989》,那个年代的诗歌运动如火如荼,我在旁观。我觉得你的写作比我早,你有一首写《旗帜》的诗,那种热情我能理解,你和八十年代有着某种关联,而当我在九十年代初进入个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时代和诗歌现场发生巨大的逆转,诗界变成了个人的寂静笃实的爱好与小小内在的革命,同时,也在对过去诗界非诗的东西进行清理,自然地尝试着新的写法。
程光炜先生在专文能及张曙光的诗时,讲述到后者参与到了90年代诗歌的整体转变,这一转变体现在后者的创作中不是通常那种爆发性的反叛性的表面形态,而是根植在后者对历史的观察和个人经验上的。我以为这是很公允的观察。
朋友张桃洲有一则谈论九十年代的诗歌长文,是一则有份量的诗学研究文献。九十年代以来的诗学写作,和八十年代自然构成了某种隔断,如同时代的分野一样,即便是八十年代写作的诗人也在完成与自成的分离。你的问题中提及到是不是一个诗学问题,这个成分肯定占重要的内容,它确实是一个诗学问题。
X:欧美诗歌及理论的大量译介,直接促成了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先锋景观,你所受到的影响有哪些?
L:我首先想到《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新西方文论选》《叙述学研究》;诗学译本对我最重要的,赵毅衡译介的《美国现代诗选》(上下册)是那些年常读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不知读过多少遍,时常翻阅,说到美国诗歌,还有另一个译本是郑敏女士编的,那些年我可是比照着阅读着它们,有一年在北大讲座上碰见郑敏,我提及她译的这本书,提问好象是我们如何从译诗中获得创作技艺,好象还问过她的写作和译诗的关系。那些年从她的《英美诗歌戏剧研究》获得诗的技艺,她的著述可读性强,言之有物,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诗学专家。
我总是这样想,一个时代的诗歌转型和译介诗人们的阅读相关,或者说它参与了诗人们的创作,这是不争的事实。张曙光的写作提供了新的东西,与他的对美国诗歌的译介有某种关系,他那些年是在译诗中获得第一手的创作技艺,我在读到他的关于美国诗歌的讲稿时,感觉他从纽约派诗歌里借鉴了新的写法;另外,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那些年真是如获至宝,就是现在也时常翻找出来重温。
确实,英美诗歌的译介对我们的阅读产生了某种兴奋感,比如运动派和黑山派诗歌的观点和作品对我的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说意象派的诗歌,说具体点,威廉斯对美国诗歌走向的扭转也可作用着中国诗作在九十年代的语言的实验,纽约派垮掉派诗人们的写作和生活对我们产生了实验的剌激,一拔拔诗人不同的写作倾向可以说更多地来自译介的镜鉴,可以说,在那些年里,我们把美国现代诗歌的历程重历了一遍,从各种流派中获得借鉴或移置到汉语新诗的实验中。
X:你客居京城十年,“客居”是中国古代诗人特别的一种情怀,一种诗歌的打开方式,你的京城客居生活对你思想、情感和写作有哪些影响?
L:1999年到了北京后,生存上的压力影响和稳定的写作环境的中断当然给写作带来了某种伤害,甚至说,在北京最初那些年写作处在停滞的状态,恢复到九十年代相对封闭稳定的写作状态已很困难,不过,在京十年那也是一个反思和累积的十年,我所以回武汉,力求想寻找一个相对宽松的压力较轻的写作环境。现在想来这外部的考量过分了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但确实经过这些年迁移折腾,到了2011年后似乎和九十年代那个状态对接上了,有写作重新开始的感觉,当然感觉比九十年代那种状态更好,更让我满意的是写出了那个环境里写不出来的作品,可以说,这些年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现在的作品。
北京的十年,用我们地方方言来说,那可是十年长学。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我的生活在近四十岁前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向,我所在的地理、身份工作人际关系状态精神世界眼界视听都发生了不得不变的转变。说到眼界,至少是从仰视到平视最后过度到俯视,你的身体和精神至少跨越一些东西,在你身处时代你的国家的首都,最后完成自己的游走,离开那里。
前两年,我到北京去卖房子,那些家俱有点不忍送人,书桌衣柜日常用品让我留恋,它们伴我经历了那些日子,它们上面写满了个人的回忆,我有些对北京割弃不下,虽然离开它到南方生活几年了,觉得对所有的城市唯有北京最熟悉,它所有的街道我都曾丈量过的,他对我馈送太多了,我说不明对北京复杂的感情,我不会轻易臧否它,我有些想重返这里,在房子出手后,我在它的郊区买了一套房子,我对朋友开玩笑说,我为自己过去的家俱找了一个空间。
在北京虽然写作的少了,但对诗艺术的视界打开了,加上我在杂志社编诗歌,很自然地要打开阅读量,我至今感到骄骄傲的是编辑了不错的诗歌作品,我以我的理解来推动中国新诗写作,我把我对诗歌艺术的理解落实到编辑工作中,为此尽过一份气力;
另外北京相对其他省份不同的,诗歌活动多,这是在首都生活重要意义,尤其是网络未兴盛的那些年,一个写作者可获得很多诗歌方面的现场经验和置身于词语空间的机会;比如说,在北大见到瑞典诗人特朗斯特吕姆的诗集发布会,在那个会场见到老诗人。那个诗会上余华也去了,记得他在台上说他写了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小说,抵不上特朗的几行诗,他把那首诗逐字逐句读了,陈述诗人协助他完成了对词语的理解;活动之后我情不自禁地写过相关随笔。那次活动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得那天从北大转车到租房,在112车上,几乎穿过了整个北京城,当子夜时分回到租房,我看见了天上的星光。
另外有一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诗人弗家-弗雷泽来了,该校搞一个中美诗人朗读会。我去了,和西川、孙文波等一起参加朗读,后来这事写入《后垮掉派诗选》的后记。这次活动被我也写进随笔《我的美国诗歌地理》,后来用在《世界文学》。
在北京工作生活,你的视野整个地打开了,何况你就是冲着在首都的这个文化优势而去的,那是你在县城小地方所渴望的空气,那里的书店那的诗歌艺术活动酒巴演出各种场合碰到的名人。同性恋者。背包的流浪者--
我写个一首未示人的诗《北京出租司机》。说句笑话,那地方的出租司机都牛逼着(他们有北京户口)他们见识也确实不同,他们毕竟在皇城根下呼吸首都的空气见识着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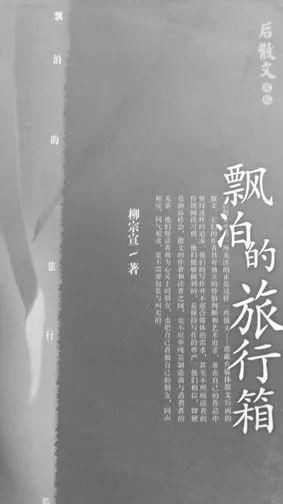
▲柳宗宣个人作品
X:九九年你写出那个时期的个人代表作《上邮局》,这首诗被评论家称之为“命运之作”,为什么?
L:这是朋友李以亮的评说,好象用在,《特区文学》好在他的文章短,我转发在下面:
“诗歌里的叙事似乎被认为是1990年代的发明,这多少有点对于文学史的盲视。如果说,自90年代始,叙事在现代汉语诗歌里才得到重视可能是确切的。也许是直觉到诗歌里的叙事与散文/小说的叙事毕竟不同,有人将诗歌里的叙事称为“伪叙事”,或者强调“诗歌的叙事性”(对应或从属于“抒情性”),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对于诗歌写作本身而言,写出好诗才是正经。柳宗宣的《上邮局》一诗,通篇以一种直接而克制的叙事,接二连三的细节呈现以及其中浸润的巨大哀伤之情,彻底打动了我。
“散文/小说的叙事大多是可以转述或者说改写的,但诗歌里的叙事不能,它具有唯一性,或者说“非此不可”的特征。当我想要提要概括《上邮局》一诗时,我发现很难,最好的办法是重引一遍,而这是不必要的。诗歌里的叙事贡献出的东西,有比散文/小说的叙事更多的不能被提炼的内容。
“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在她的专栏文章里曾以一个无名作者的诗歌为例说:你的题为“这里”的一首诗,只是对一间房子和其中的家具所作的最常见的散文化描写。在散文里这样的描写起到一个具体的作用:它们为到来的事件搭起舞台。某个时刻门将打开,有人会进来,有事情要发生。在诗歌里这样的描写自身必须“有什么发生”。一切事物都要起作用,都要有意义:意象的选择,处置,它们在语言里采取的形式。对一个普通房间的描写出现在我们眼前时,必须成为对那个房间的发现,对那个房间的描写所带的感情必须能够与读者分享。否则散文依然是散文,不论如何努力地把句子分成行。更糟的是,在那之后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上邮局》一诗正是这样:它的每个场景每个细节都是“自身有什么发生的”,都直接指向人物命运的呈现,指向对生活、生命的发现。
“诗歌的真实性,传记性材料的运用,富于张力的情感,质朴到容不得半点伪饰的语言,克制到近乎零度的抒情(冷抒情),这些都使其诗成为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一个诗人一生里真正能够成为“命运之作”的东西是不多的,而《上邮局》这首诗应该担得起。

▲柳宗宣个人作品
X:《上邮局》不仅仅是一首一般意义上好诗,更是当代汉语之美的一次结晶,同时,透过这首诗,还可以窥见你诗中特别蕴含的伦理矫正,请你谈谈在这首诗的写作中,你的情感状态和修辞策略。
L:你所言的结晶,言重了。这首诗算是我在九十年代写得最好的诗作之一。在九十年代那几年经过新诗的练习能完成这首诗作也是不易的,你不知我最初的写作水平多么低劣观点多么陈旧,在那几年能完成自我更新真是下了大的功夫的,你要知道我是二十七岁开始写作,不是天才性的写作,早年读过中文专业,一些既定的框架性的理念先入为主地占据了自己的头脑,要从事新诗写作完成自我的更新是艰难的,好在那些年能算如愿地完成了这项必须的工作。那些年身体力行的诗歌写作让我想着离开生活的小城,近年反观那些年的状态,可能是我无法忍受在那个环境里生活,我这个人既能忍受,也有一种牛劲,我性情峻急,不能容忍平庸封闭死水一般的生活,你要知道那些年有着逃离的冲动,在我读到兰波的诗歌和书信颇有感应,我注意到了兰波他逃离小城要经过的那个火车站:夏尔维勒火车站。
我的逃离是从死亡那里获得力量的。所以我在这首诗中写到了已故的父亲,父亲往往在我对人生进行某种选择时来到我的梦中,它虽然死去多年但参与了我在世的选择。这首诗是我从北京回小城好个书房里写的,当时写得泪流满面,但语句很平静,我在书写的时候抵制了情感的干扰,我把我的出走和父亲的自杀交织着叙述,前大半部分觉得满意,后部分有些情感泛滥,好在给后面一些句子给平衡了。
我的学生曾提及到这首诗里的手法很多,说有超现实的写法,我说没有啊,他摘出了这样几句来旁证:
那是1999年10月20日正午
逆光之中的石家庄火车站
一个人和进出的游客交错走来
父亲,你突然站在了我面前
X:道德伦理维度的缺失是当代中国诗歌写作大面积存在的,但你的写作却非常关注这个维度,请你谈谈在这方面的思考。
L:我这个人老派,情感道德都受乡村民俗的影响,人活得蛮严肃的,这可能与家教有关,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就像我的胞兄一样过于正派,虽然读了很多译介的书,但骨子里还是保留乡村家族遗传的血脉和精神;你要知道,我毕业后一直在教书,这也自然规约了我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取向,又加入文学阅读的美育。我这个十分善感,悲天悯人,仇恨,总是仇恨不起来;李以亮在我为女儿结婚举办的小型酒会后,专门谈及我的几首诗:我也把他的话转录如下,可代我回答你的问题:
“柳宗宣的近作中,我特别看重《给女儿书》《给女婿的谈话录》等一组诗,因为我在其中看到,诗人着力恢复我们诗歌中的伦理维度的意图和实验,而且,这实验是相当出色的,既表现出真实动人的情感力量,也体现了现代诗必要的艺术性。不讳言地说,种种标榜“先锋”、实际缺失了伦理维度的“诗歌”写作,已经不仅使大量读者发生了对于现代诗的误解和不满;更有甚者,部分写作者把诗歌艺术的“非道德化”倾向异化成了“反道德”的自我作践,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诗歌绝不可能给予任何人带来道德豁免权,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在这样的语境里,我特别欣赏柳宗宣在“道德/伦理化”的诗学及时的矫正力量。在此,真正考验诗人能力的问题在于,如何将道德主题有效、艺术地呈现?柳宗宣在这一组诗里,调动了人至中年的深厚积累(无论情感,阅历还是思想的)。说到底,就是构成诗人“主体性”的综合因素。有人总是试图回避 “主体性”在诗歌写作上的根本作用,或是借口诗的自足自律性,或是一直淡化甚至不承认思想性、精神性之必要(只强调所谓潜意识、生命直觉等等),抽象或泛泛地谈,我当然不反对这些“理论”的合理性甚至深刻性。但我想,它们尚不足以彻底颠覆主体性,毋宁说是对真正的主体性理论的补充与深化,舍本而逐末是容易的,也是可笑的。《给女儿书》《给女婿的谈话录》等诗,都是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以娓娓动人的叙述,直抵人心;是关于情感的,也是关于道德的;是对话,也是自语。所以特别真诚,质朴,剔尽了修辞的虚饰,没有华词丽句,却有大美,题旨无不涉及人生的大道,却又没有丝毫的说教。”
另外,程一身博士的短评也提及到相关的内容,他这样写道:在写作风格上,我感觉柳宗宣是个非常接近希尼的诗人,他始终直面并力图化解爱,尤其是两性之爱与亲人之爱的难题。像《宿疾》呈现的复杂经验,尤其是《给女婿的谈话录》,在我的印象里应是中国诗人首次富于深度地处理这种独特的家庭伦理题材。

▲柳宗宣在中法音乐诗歌节朗诵会现场
X:2012年是你写作的标志性年份,从这一年开始,你写出了一批自我更新的作品,这批作品的个人风格更加鲜明,请你谈谈从这一年开始,你的写作里都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内外在依据都有哪些?
L:你问的很好。2012年确是我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一个人在海口过了春节。我完成了个人生活的逆转。初到武汉来,最初几年过得不顺,因为你不能面对一张平静的书桌,我对自己说,再不能被外在所裹挟,内心的呼声我听到了,我要写诗了。
2012年是我写作中少有的井喷状态,那年几乎就在写作状态中,我的写作如同得到神灵的支持,几十首诗就出来了,可能是十多年的南北迁移外部影响,北京时期的断续写作变成了专注的状态;诗的气蕴完全有别于北方时期,诗的空间向度悄然变异,相对于九十年代在小城的写作,我很满意自己的在五十来岁时诗写作进入高峰阶段,或者说自己有幸能在词语中完成自己的夙愿。
有时候在汉口自己的新居的阳台上观望小区外景,很自然想起九十年代我在潜江小城的寓所的阳台上的情景,生活似乎在重复,但人的视域更多的发生了类似于外部生活的变迁,词语的时空拓展开来了,技艺也丰饶多了;当我编辑新诗集《河流简史》时我将这一年的写作放在前面,看到第一辑中的诗作,人觉得蛮安慰,历经了多年的折腾,命运回报了我,通过诗歌作品。
至于诗中出现哪些变化,我与木朵的访谈里都涉及到了,这个访谈附在了诗集的后面;现在细聊来,2012年开始的写作一直持续到2015年,我写作的《平原的雨》《孤岛》《宿疾》;诗的生成技艺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你可以比照下我早年的诗作《她穿过黑夜的楼顶回家》和2014年写就的《夏日时光》会发现写法上很大的差异,虽然它们都关涉到诗的叙述。
反观近作,有的诗作容纳多年累积的词语场景意象和主题,一首短诗变得时空交叠融入了写作者一生的收藏似的,这时候的写作有点像挖掘,在向个人生命的内里开挖;好象在重写过去,一首诗几乎容纳了多首诗,如《孤岛》一诗,好象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它,现在总算完成了它,人获得了无比的安慰安稳和欣悦感。比如燕子一诗,早年写不下去的草稿丢弃在那里,但现在忽然被写成了。
有时翻阅这本诗集,觉得特别让我珍视,觉得诗触及的个人生命的丰富,词语的触须向不同的存在伸展,如《一意孤行》《禅寺午餐》又如《平原歌》,一个年近晚年的写作者完成着他写作的丰盈。生活写词语的关系独立平等又相互促进。程一身博士说我写作的是自传诗,也可成立,但我的写作可不是美国自白派翻版哦,它里面融入了不同的技艺,它有写作者自已的调性,我的诗可不那么自白,甚至他反对自白的直白。如果要往深处说,我还是倾向于西尼似的写作,个人经验。唯美兼智性。
X:你的诗作多贴近现实生活,用的也是日常语言,情感中立,不轻易拉起来,但读后却往往能让读者感受到个人经验和普遍经验、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平衡,你对这种平衡怎样认识?在诗艺的层面有什么秘密?借此也可以谈谈一般意义上的好诗、重要的诗和个人风格之间的关系。
L:我的诗集让张曙光写序我是有考虑的,他的文章也写的中肯。因为我们都关注诗的日常;但诗又不能停在这个日常,如张曙光有一首诗《给女儿》谈及的是他的往事,农奴制。中世纪的历史。死亡。最后一句是,我将坐在阴影里\看着你在阳光中嬉戏。
我也有一首同题诗,写得是多年来和女儿生活的日常,组织在词语的调子里,我的视域就不那么形而上,虽然里面隐含着一些超越性的元素,比起曙光兄的诗对普通经验的关注弱多了。如果说我例举一首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诗就是《孤岛》,此诗的具象和抽象是月光和水的交融,它们二者之间是生成的关系。
我的写作在意从具象进入,我反对在诗中说教什么的,就像水里有甜味但见不到糖一样地在自己的诗中注入形而上,但它看不见,你只能品味它,你只能从水里品味;在我想来,好的重要的诗得有写作者个人的现场经验和日常的元素,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建立不起来。
我蛮喜欢你的那首诗,一直想解读它,那首诗写早起开车前行到某地去,我想诗得有场景人事,一切得从此生发。

▲柳宗宣与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
X:你是说我那首《今晚我必须到达临邑》吗?那首在我的写作中却并不典型。现场经验和日常元素在我的诗中并不是大面的陈列,我更喜欢靠一种语调把它提示出来,我喜欢那种形而上下之间自由往还的格局。
L:我在意你这首诗,是因为这首诗让读者触摸到了诗的现场,那从具体中散逸出来的抽象的情感和词句间的呼吸。我说我要解读它,因为他为我对诗的理解提供了例证。现在想来,我在诗的叙事抒情做过实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呈现可触摸的诗的空间,这可能是从拉金诗歌阅读中带来的启发,让诗更有感性,说实在的我在诗中如何拒绝抽象空洞;即便情感也得在一个空间中呈现,当然,诗的叙述是有多种技艺来助成的,诗的新的感性也是和种元素来凝结的,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所以说我喜欢西尼的诗,他的智性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从他个人特别具体的词语空间里透显出来的,它们是有机的一体。没有个人,风格就谈不上,没有写作者个人的情感、倾向,那所谓有风格就出不来。从金斯堡我们欣赏到他诗中的有节奏的性情,他的技巧和情感的融合;从罗伯特勃莱我们发现了诗中的层次(或多重建筑)从拉金的诗在意的是它的有人事的场景,他们写作个人的诗歌,我喜欢诚实的风格,我总在诗歌里辨析诗的语音诗人的日常场域他的具体,从此来观察或触摸一个诗人的弹跳力他的超越和视界。
X:你刚才谈到西尼的智性,智性是现代诗重要的元素,但我却同它很隔膜,你不妨谈谈它。
L:西尼的智性,与他的学者的诗学研究与关,你看他的关于诗人们的评说论文多么耐读,如他的《论舌头的管辖》最后论及他喜欢的诗人毕肖普,他既有学者的视野与专业能力和精神,还有对个人日常生活提炼和想象再现的能力;我无法用言语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这种尊敬甚至转移到了译介他诗集的雷武铃身上,我以为雷武铃之翻译西尼是可靠的,他们之间也有神交。
X:你的诗日常但不零碎,含蓄、克制但生存的严峻自出,语言与你个人的生命状态之间有一种自洽,这是一种很高的写作境界,请你谈谈写作境界与个人才能、人生处境、精神成长之间的关系。
L:因为我们当代诗人注重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观照和提炼,诗就不会零碎,它是组成诗中的一个意象和元素。一首诗就是词语的组织,而情感因创作者的语调从词句句群中透出,这样如你所说,语言和个人生命之间形成一种自洽。
我有一首诗《燕子燕子》,写了很多年,早年处理完后总觉得不如意,后者不忍读它觉得把这这首诗写废了,就丢弃在那里,有一年也就是2014年我正在写一些新作,状态蛮好的,忽然想到要重写这首诗,一些句子冒出来了似乎催促我再写它,这样我又把那旧稿拿出来,改写,几乎是全新的词语构架,在这首中就融入了个人南北生活的现场。这样很自然地透现出我们存在的境遇我们的精神气息,在诗节的生成中。
一首诗最终生成和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之间确有着某种联系,它在你的身体里在长成,这需要时间要找到它的契机,它和你创作者的技艺精神理解力都有关系,不然它不出来;它是一个写作者整个存在的外显但又独立于写作者之外,它借由你将它完成了。
X:你的诗作在叙事、情感的处理上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请你谈谈在这方面的写作经验和认识。叙事是一种表达的手段,是为纠正抒情的空乏而生,但弊端也随之而来,你在运用这一手段的时候,都注意了什么?
L:有次在廊坊学院的讲座上这样讲过:现代诗的叙事和情感是相融在一起的,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的现代诗脱离了虚幻的抽象的表述,加强了可触可感叙事因素,使诗拥有了它自身的肌质和呼吸;诗歌的情感的传达和事件纠结在一起,让你分不清哪是叙事哪是抒情。情感和叙事是无法分离的,诗本质上是情感的,同时它又是事件,诗就是一个混沌的存在。
新诗从叙事随着诗的后现代化进程而来,这使诗的客观化的样态出现了。早年我说过这样一个句子,我愿写出能够看见的诗歌,也就是说在意诗的客观性,诗的情感也是有空间的,或者说诗的情感也是可以能看见触摸到的,这是从现象学获得的观点。九十年代的写作者们他们融汇了译介到国内现象学的理论,他们在写作中悬搁了创作者的主观判断,让事实自我呈现;其实诗的客观的叙述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所谓叙事也往往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或显或隐的双重叙事,其实,诗的叙事是一种伪叙事,其实是抒情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对我们以前抒情方式的某种抑制。
在写作中出现的叙述试图还原诗的语言的天然属性,这完成了诗歌语言的形而下的滑移过程,也实现了对当代诗歌中语言暴力的消解,这是九十年代以来诗歌所进行的重大的转向之一。
在九十年代个人的写作中,诗作中的叙述因素加强了,和当时的诗歌氛围是吻合的。我的诗作《她穿过黑夜的楼顶回家》《一个摄影师冬日的漫游》叙事的风格透显出来,在我以后的《母亲之歌》中由叙事转向叙述,你说我的诗中含蓄克制,可能与叙述有关。可能如你所说的,加强诗的叙事一些弊端也随之而来,往往会出现粘滞板结的现象,失去诗的飞行能力,但是如果你运用得好,你将叙述当成诗的生成手段之一,你融汇其他技艺,这个毛病会克服掉的,这不是诗途述的问题那是我们运用它的人的问题。
如前所说,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在诗中叙事也是和以往新诗写作的一种分野的元素,好多学者们都论及这一点。也这成为诗界内外人们的垢病的话题,但我以为诗的叙事古以有之,你看贾岛的《寻隐者未遇》无一句抒情,就是叙事,事的组合和拼接。人们对新诗中的叙事有些反映过激。古诗中可以叙事新诗难道就不可以运用这一古老技艺?!
有次我在一次讲座中论及诗的叙事时,引用过黄灿然的一首《亲密的时刻》。诗叙述的是诗中的“我”去看望医院中的父亲的事象。在讲座上读了这首诗,事后一个中文系的老先生找我要这首诗,他可能被感动了,他可能不再非议新诗的叙事了。
其实,诗中的叙事是新诗谋求自我解放的方式,如同朱自清说新诗的发展就得靠自身的散文化。关于诗的叙事,我是用了一些精力来想它的,所以细读过关于叙事学方面的理论,对它的理解也在更新着加强。
须知,叙事让诗有了更强的包容力,让诗呈现它应有分量,不致落入轻飘飘的情感表达的窠舀。我在评述续小强的诗集时,曾详论过诗中多重叙事,这其中包含两个或多个同等重要性的共生的情节,还有次生的对戏剧独白的倾听与处理,对多种声音或语言情境所做的自我叙述--对诗歌情境开启的可能性,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实现的与未实现的、细微的或可能遗失掉的事态的多位组合叙述。
X:叙事元素的加入,让你诗中的日常经验和语言现实发生了哪些改变?
L:我在诗中加入叙事,后来写作日益明显,由叙事到叙述,它让你的日常经验的事件更多的融入到诗中来,你的语言与个人日常发生了某种必要的磨擦力,使你的诗作更有现场感,更有包容力,它把诗的领域自然给拓展了;这个话题在和与木朵的对话中曾论及到;随着写作持续的反思,随着个人对文本意识的加强,到了2012后的写作,方式有些变化,诗中的叙述不拘泥现场或事象,它加入了多重的词语的想象,或者说它是一种词语的组织,与外部事实不形成沾滞关系,诗的语言现实变得更独立,从外在事实到诗的语言现实的落实,这里需要诗人提炼能力和对语言的尊重,我有一个从前者挪移后者来的能力,语言的能指功能的加强让语言形成它自身的运行。
X:事件(事情)与情感思想的表达在你诗中是怎样一种修辞关系呢?
L:事是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的“事”:右上边是一个捕捉禽兽的长柄网,其下是一只左手,表示手执捕猎的工具去猎物叫事;情,从心,在说文解字中指的是人之阴气有欲者,我们可以感知到“事”和人的身体发生着关系.它牵动着人的情感;手长在人的身体,和人的心相关,情在事中,事由情来呈现.这是我以前文章中片断。
现在有些人的写作把身体和语言的联系中断了,你看不出他的语词和身体的关系,当代文学写作最大的困境是身体的失踪。而我们的语言和经验是从身体里生长出来的,诗歌中的叙事和人的身体发生着关系,和人的心情感发生的联系,诗歌中有了事,有了情就有了身体,有了感觉,才是活的充满了生殖能力的诗歌。
毕肖普在一则访谈中他有过这样的话,她说,要多少事才能成就一首诗啊。诗的叙事其实是事的组织和粘贴,在词语中的挪转中断和呼应,它融入到词语空间中里,我现在的叙述的空间变得绵密,往往在词语间的时空在交织出旋律,不知你注意到《夏日时光》没有,那里就画面的组合。如前谈及到的《燕子燕子》一诗,诗的叙事粘贴隐匿在一个诗的旋律的变奏中了。

▲柳宗宣在深圳读书月十大好诗获奖现场
X:你的《鱼子酱及其他》这首诗获了一个在全国很响亮的诗歌奖,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L:这首诗获奖就像我写作它一样意外,不过,细想起来不意外,是自然而合情理的事。获奖后,诗人木朵和教授魏天无著文解读过这首诗。
有一个诗人用微信方式自发地向我传过对这首诗的印象。在微信中他这样写道:鱼子酱好,当下与历史、现实与文本的交织和涂抹,让我想象到布罗茨基,大口咀嚼流亡的面包。
在领奖会上,我遇到评委吕德安,人们说他少言少语的,但我看他蛮诙谐健谈的,当我们在圆桌酒宴上用餐,他突然转过来说,他对我的鱼子酱投了一票的。他说他读到这首诗时,以为是一个更年轻的人写的,语言推进的节奏的平衡能力很讲究的,但诗的指向语言的深厚度不像一个年轻诗人所为。

▲柳宗宣与诗集日译者竹内新在一起
X:我很高兴他和你说这些,这首诗没有这些年的生命体验和认知,是写不出来的,我读后感觉这是一首味觉、政治与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复杂而又单纯的好诗,你对此诗的写作怎么看。
L:这首诗里你说及政治和一个人的命运,我们的生活与阅读的交织互证都在这首诗里出现了,它看似单纯却是复杂,这又得重复之前的话题,没有我对在首都的生活经历的反思个人命运的思考和在对俄罗斯诗人的苦难经历的阅读,这首诗的情感就出不来,也不会去写就它,另外没有这些年对诗技艺的揣摸和实验,这首诗也生成不了,也不可能这种方式去呈现它,确实,诗的语气的转换和意蕴的递进都要写作者的控制和平衡能力。
此诗获奖后,我的大学的同事们教授们问我,诗句为什么都是双句,为什么要那样转行。我不得不做一些新诗的普及技艺的普及工作。我在意的是这首诗让自己吐了吐气,是的啊,文本与现场的交织和涂抹。没有个人现场彻骨体验和同声相求阅读思考,这首诗就出不来,我的学生读它觉得困难,因为他们对诗中涉及的异国人事和途述文本有隔膜,这首诗挑战确实挑战着读者的阅读视野和新诗的审美惯性,虽然他们多么爱吃鱼子酱。

▲柳宗宣书房一角
X:你以诗集《河流简史》总结了你最近十年来的写作,关于未来的写作,比如在写作方式上,场域上,风格上,你有什么新的追求和憧憬?
L:可以说,现在是此生创作环境最好的时期,在我过了五十岁后,工作上和自己的诗歌爱好相关,我供职的大学为我弄了一个新诗研究所;我按自己的趣味编着一本新诗读本;我有家室但无家室之累。唯一的女儿也成家工作有了他的房子和儿子;现在钱不多但也有余钱,不必受此催逼或压迫,我拥有个人支配的时间,时常在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
但人状态不会好到哪里去,生活不会越过越好,人在世就是在走向衰败,无论你在什么情状里,现在我又有了时间的焦虑感,觉得你的那么快逼近老年,人真是活不了多少年,你所做的事情正开始展开但你的精力你的身体再走下坡路,觉得供你支配的时间不多了,你得像冬天一样隐藏,蛰居、收束时间和精力,用在个人重要的事情上。
弗洛斯特在他的校园谈话中这样说过,当你的兴趣有所拓展时,你的藏书就可以适量增加一点。近些年来,我的藏书不减,对语言的反思多了些,作为一个写作者这应当是一个不辍的功课,由阅读带来的对语言的思考纠缠着我的意识,近些年,读着福科,布朗肖、德里达等,他们对语言的理解让我有触动,引发我如何理解语言并尝试着将新的方式引入写作中来。
在他们看来,语言不附带主体性因素,也不及物,语言自我呈示。在福科的《词与物》中,他所论及的语言折向自身,仅仅讲述自身的形式;语言在自我振荡和自我发光。
在他们看来,人从来就不是一个说话的主体,语言的自主存在就意味着说话主体的消失。福科有句名言,作者之死。
在布朗肖的《文学空间》里,他论及的诗的语言,他说,“语言作为本质的东西在说话--不应让任何人来说话--说话的不是马拉美,而是语言在自言自语。”
写了几十年的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不断地面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的认知不得不关注,越来越深入的,随着这种认知,我们的写作会发生变异。
我有习得的偏执的观念,就是要改变你的语言就得改变你生活,我生活的努力改变都是为了写作或语言形式的变化,比如,我现在在山里盖房子,料理山居生活,试想一个写作者外部生活发生了变化,可能会影响诗歌的生成,至少为诗写作提供某种契机;我想着如何找到新的方式来认知或进入语言,这是本人乐此不疲的事情,虽然诗歌有着它自身的命运。(完)
人物介绍:
雪松,姓名赵雪松,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诗人,兼及散文随笔写作。出版诗集多部。现居山东滨州。
柳宗宣,1961年出生于荆州国营后湖农场。当代诗人,新散文作家。曾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杂志诗歌编辑多年;曾获深圳读书月2016“年度十大好诗”奖。诗作译介到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现为江汉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主编《新诗学》,从事诗学研究与教学。
封面占领计划
第二期来啦~

第二期的主题为:新年心愿~小伙伴们有关于学校的风景、关于家乡的风景,最美宿舍照、最美全家福,最美基友照以及你最想说的话发给最最,所有你觉得能代表新年新气象的最最统统帮你上封面。
发送格式为:你的封面照片(横向构图)+你的新年心愿+你的微信号
发送邮箱为:zuiwuhan027@qq.com
everybody来来来
来给最最投稿吧~
采用有稿费!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站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