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旅行记
广州旅行记
梁玉美
月台
朱自清的《背影》里,其中有一段写父亲到火车站送他,穿着黑布大马褂的父亲蹒跚地爬过月台的栅栏去给他买桔子,那之前的我没坐过火车,觉得月台是一个
广州旅行记
梁玉美

月台
朱自清的《背影》里,其中有一段写父亲到火车站送他,穿着黑布大马褂的父亲蹒跚地爬过月台的栅栏去给他买桔子,那之前的我没坐过火车,觉得月台是一个与送别和爱有关的地方,后来在大街小巷听到台湾歌手高明骏一曲撕心裂肺的《站台》,那时的我也还没坐过火车,却感觉月台是一个与爱情和等待有关的地方。
这一生坐火车的次数不多,每次坐火车,一进站就想到月台这个词,好几次去找寻那月台上的栅栏究竟在哪里,终是没有找着,倒是高明骏歌声里那个长长的站台一直都在,甚至是更长了,而寂寞地等待的那个人早已不在原地,目光所及之处,尽是匆忙赶路的人群,这时的我,总会是有些失落的,想着会不会有一个人,买了月台票,来一场缠绵悱恻的送别,又或者,演绎一场涕泪横流的重逢!
现在的火车站,已经不再出售月台票,也没有了叫月台这样的地方,取而代之的名称叫做站台,而我,却固执地在心里把这个上车的平台叫做月台,它和是否能赏月无关,却与我想像中那些悲欢离合的情节有关!

列车
“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自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宫崎峻《千与千寻》里的这句台词,每次都会读到泪流。年少时坐火车,我会去观察前后左右座位上的人,想着哪一位会在中途下车?哪一位能陪我坐到终点?哪一位又会是单调的旅途中能聊上几句的知音?渐渐年长,渐渐世故,再坐火车时,依旧会观察前后左右的人,前排戴墨镜的小伙看起来不像好人,左侧过道边上的那一位正不怀好意的与邻座的姑娘搭讪,有人途中下车,我得看好自己的行李……常常为自己无端的警惕脸红,可还是回不到年少时的单纯。
在早春的时光里,从贵阳北站坐上驶向广州的列车,贵广高铁以每小时200多公里的时速自贵阳一路向南,看着车窗外飞快后退的房屋山水,我似乎也看见了时光的飞快流逝。
列车进入桂林北站,广播通知将调转车头行驶,乘客在列车员的帮助下一边调转座位,一边开始窃窃私语,想弄清楚调转车头的原因,我想到了詹天佑京张铁路的之字形设计,大概也是差不多的原因吧,后来百度了一下,因列车到桂林北站是绕道了,所以需调转车头行驶。火车前行的时候有转不过去的弯,人在前行的途中,也会有转不过去的弯,有时候,调转方向不一定就是后退,换一个方向,依然能够前行!
四个小时的时间,列车准时抵达广州南站,出站,排队,塞车,折腾到六点半,到达天河区南二路预订好的酒店。

沙面的怀旧时光
广州沙面,曾称拾翠洲,因为是珠江冲积而成的沙洲,故名沙面。鸦片战争后,清咸丰十一年后沦为英、法租界,因此才有了现在的国家5A景区,有了露德天主教圣母堂、苏联领事馆等洋楼,对于景物,我一直是没心没肺的,网上有人专门批评我这一类人的:“你说你想去卢浮宫的金字塔博物馆,看到了达芬奇、梵高、毕加索的画作,可你对欧洲艺术又有多少了解?你说你想去布达拉宫拨动转经轮,可你并没有任何信仰,你觉得你去了西藏真的会受到心灵的洗礼?”,我只想说,我就是想去我去过或没去过的地方走走而已,别上升到哲学的层次,我走过了,我高兴了,我回来后认真工作,认真赚钱,然后去下一个地方,有什么不可以呢?!
去沙面的这个早晨,就是这样的心情,广州早上八点的阳光洒在身上,没有想像的那么灼人,同事好友一行六人,从天河区的体育中心打的直奔荔湾区的沙面,只为了在大量的游人到来之前感受慵懒的怀旧时光,一路走走停停,拍拍美景美人,留下的欢声笑语才是回忆里最重要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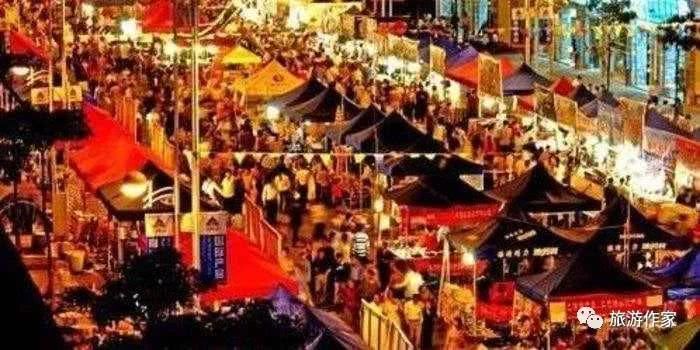
广州美食
写过一篇《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的文章,把美食与爱相提并论的背后,足见本人对美食的免疫力之差,于是,出行之前,查攻略、搜地图,一切都只为满足对美食的专注和痴迷。翠华餐厅,是香港著名的连锁茶餐厅,也是港式饮食文化的代表,酒店楼下的底层就有一家,逛街累了,进去喝一口浓郁的奶茶,尝一口喷香的菠萝油面包,不用到香港就能享用地道的港式风味美食;与酒店一街之隔的广州酒家是羊城的老字号,对于贵州妹子来说,正宗粤菜就别去尝试了,单单一顿早茶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彻底沦陷,虾饺、榴莲酥、叉烧包、萝卜糕、肠粉……味道很赞,最重要的是每一道都很精致,比起贵州家乡用大海碗盛上来的牛肉粉、肠旺面,确是不同的风味!
旅行于我,不在于去了哪里,也不在于见到了怎样的风景,而在于旅行的过程让人放松和快乐,旅行之后的回味亦是必不可少的,人懒的时候,翻看一下拍下的照片就很满足,心血来潮的时候,把旅行的过程和心情变成文字,让一切在流年里慢慢积淀成一路的风景。按部就班的生活,可以让心平静安稳,而旅行的日子,却可以让我见到更多的不同,感受更多的别样人生。

梁玉美,笔名玉心,1972年6月生于贵州开阳,现居清镇,清镇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14年开始创作,有散文和诗歌作品散见于《贵州作家》《贵州都市报》《黔中早报》《湖城艺苑》等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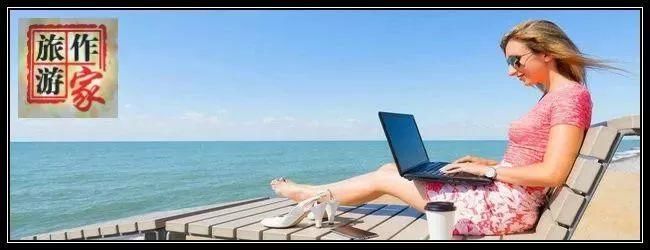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站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