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去旅行
被旅行改变的 荒野气象台 亲爱的读者: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向大家介绍和推荐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旅行目的地,甚少谈论旅行本身。关于旅行的意义,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答案。但这个答案
被旅行改变的 荒野气象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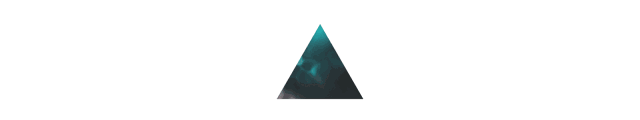
亲爱的读者: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向大家介绍和推荐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旅行目的地,甚少谈论旅行本身。
关于旅行的意义,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并不总是牢固的,时不时会被不同的声音所影响、摧毁和重建。
今天推送的文章是一篇专栏,在介绍了那么多地方之后,正好可以用它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为什么去旅行,又可以怎样去旅行。
台长
▲
近几年,中国人的境内和境外旅游人数和次数一直在不断增长。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联合发布的报告,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了1.3亿人次,比上一年增长了7%。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许多东西来得太快,人们还没来得及思考那些东西的意义。旅行似乎也是这样,和旅游人数一起增长的,是社交网络里人们对旅行意义的讨论。
前不久,腾讯·大家的微信公众号上相继发布了两篇跟旅行相关的文章,标题分别是《去再多国家旅行,也不能让你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和《去了90个国家后,手机却让我变得无趣》。
这两篇文章已经发布了一些时日,但它们讨论的话题是有意思的,也让我有一些关于旅行的想法想去表达。

@Jfhoode
对于前面第一篇文章标题里所表达的意思,我其实是持不同意见的。在我看来,大部分时候,旅行都能让一个人变得有趣。就像读过一本书,总比没读过要好;看过一部电影,也总比没看过要好。旅行也是一样。不同的是,书和电影能分好坏,但旅行目的地却各有千秋。将不同地方的景观面貌和风土人情横向比较,总能得出一些有意思的见解和收获。
只不过,这种变化并非迅猛,立竿见影甚至翻天覆地的,而是一点一滴,低调而确凿地隐藏在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察觉的细节当中,更无法通过三言两语或朋友圈里的某条状态来准确判断。
另一方面,我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对于“有趣”的定义是什么,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当朋友去远方游玩,总能带回来一些让大家听得饶有趣味的谈资,甚至连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当地见闻和自我感受时的神态,就让人看得开心。
我想,一个人和他所讲的故事是否有趣,不但跟那个人自己有关,也跟聆听者有关。

@justinmclean
但在旅行带给人们的所有价值和变化当中,“有趣”简直是最不重要的。即便是那些渐渐感觉到麻木的资深旅行者,也不会否认多年以前的首次远行对后来的自己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而且一个人开始旅行得越早,旅行就越容易对他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旅行最大的价值是让人们见识到不同的可能性,并向他们提供不同的选择。最后的选择结果其实是非常私人的,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但有得选和没得选之间,本质上完全不同。
旅行之后,不管是想要继续前往更远的远方,还是更加珍惜原本拥有的生活,其实并不重要,也没有好坏之分。重要的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所有被安排好的结果。

@Jordy Brada
我们崇拜一些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为他们曾经走过的壮阔旅程和他们对所经之地引人入胜的描述深感叹服。我们还喜欢传诵一些名人关于旅行的见地和话语,并把它们当作自己前行的指引和灯塔。
法国作家加缪曾经写道:“旅行中没有欢愉,我更把它视为灵性测试的机遇。如果我们通过文化理解了我们内心最深处感知的练习,关乎永恒,那我们才是为文化而旅行。”
美国作家保罗 · 鲍尔斯也在他的小说《遮蔽的天空》中说:“ (游人)毫不质疑地接受他自己的文明;但旅行者不然,他会比较自己的文明和其他文明,并排斥那些不对自己胃口的元素。”自此之后,所有在路上的人都在用这个标准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划分。

@Chris Week
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厉害而且很有道理的样子。但问题是,《遮蔽的天空》出版于1949年,而加缪也在1960年便已辞去人世。至于我们所推崇的马可·波罗、哥伦布、麦哲伦、达尔文、斯文·赫定、毛姆,则是更早之前的人物。
当马可·波罗在元大都被忽必烈汗隆重接待时,西方对于东方的认知几乎只存在于想象中;当哥伦布从西班牙扬帆起航时,整个亚欧大陆很可能无人知晓美洲的存在;斯文·赫定在新疆和西藏遇险的时候,那片地区许多地方几乎还没有人认真探索过。100年前,被挖掘的知识远没有100年后的今天丰富,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的交流也不如今天密切。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旅行可以是了解未知最直接的一条途径;而今天,这个世界不为人所知的角落已经所剩无几。
曾经人们通过旅行中学习到的东西,现在的人有更好的途径去更便利、更充分地了解。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我们可以轻易接触到过去的人所无法想象的丰富知识。甚至不需要主动去搜寻,每天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信息,潮水一般涌入我们的视线。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也早已从骆驼和马变成了今天的汽车、火车和飞机。当年斯文·赫定需要花一年半载才能到达的目的地,如今我们只需要几个小时,便能快速到达。
今天的信息环境和交通条件跟过去早已大不相同,但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遐想去期待旅行?

@cikstefan
正因为世界早已不复当初的混沌未知,旅行也不妨可以变得更加具有目的性或更加随性。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下,无论是去意大利细究古罗马的兴盛与衰亡,还是去东南亚享受热情的阳光和海滩,只要计划得当,都能做到举手投足般便捷而廉价。过于计较投入和产出,不免显得寒酸。而每次出行都期望带回一大筐足以成书的素材的野心,也并不比在朋友圈里炫耀舱位和酒店更不功利。
旅行本质来说是一件极其私人的事情,“有趣”与否,反倒取决于外人的评判。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看到自己想看的风景,这样的旅行就很有意义。费尽心思想变得“有趣”的样子,反而很不有趣。
即便旅行不一定能让一个人变得“有趣”,旅行本身就已经足够有趣。在菲律宾薄荷岛追逐跳跃的海豚,在日本长冈看一场眼花缭乱的烟火大会,在尼泊尔博卡拉走一趟安娜普尔纳大环线,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坐船从亚洲到欧洲……单单这些体验本身,就足够值回那一整趟旅程的全部花费。我唯一能想到旅行的坏处,就是去过巴黎之后,再也不想回到老家那套由父母负责装修的房子。

@bill_bokeh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朋友,名字叫樊小八。她也是一名旅行者,几年前离开北京搬到了大理,当起了自由摄影师。最近她突发奇想,用延时摄影记录下每天的日出。
她说:“这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做一件看上去似乎毫无意义的事。没有了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的机会,没有了晚归晚睡的奢侈。但是只有自己知道,获得了怎样的珍贵。”
而我也总是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人类哪里来的资格,去轻视静谧得让呼吸都变得细微的森林,悬崖深处奔流而下的瀑布,极地边缘每一抹极光的闪烁,和从未曾失约的日升日落。
以下是她经过30天不间断记录的结果:
正在放映
樊小八·大理每天的日出
http://v.qq.com/x/page/a06672o39uq.html
编辑、撰文:潘尼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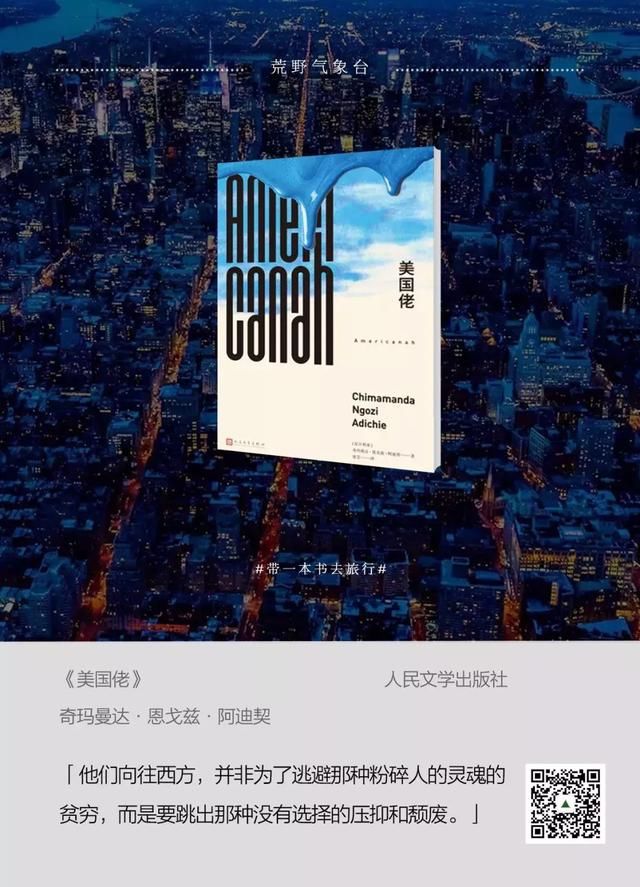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站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